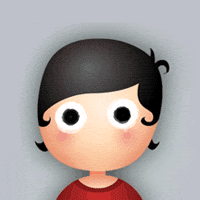吉普车勾起的回忆
雪安理
世界上,吉普车响亮的声名相传已有84年历史。我要说的一辆吉普车以及所经历的人和事,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凡人琐事的沧海一粟。故事的当局者、旁观者都是见证者。
上世纪80年代,高邮各部门、单位有小车的很少。我供职于文化宫,。一天,副主任陈国松对我说:“我们文化宫剧场虽然在全城数一数二了,但要保持演出不断,必须常外出看戏,把好剧团请来。如果有一部小车,既节约差旅费,又省出了长途奔波的时间,该多好啊。”我说:“想法是好的,现在没有条件买车。”员工李金山说:,能不能把他们的旧吉普车买来?”
在我授意下,陈、李二人去找陶有仁局长,请他把旧车作价处理。陶局长说:“你们再穷,总不能一毛不拔吧。不给一万,八九千还是要付的。”老陈说:“你们新搞了个会议室,我们单位拿一部彩电和一部放相机,跟你们换车吧。”陶局长说:“开什么玩笑,你们那是旧设备了。”老李插话了:“我们彩电是‘松下’牌,正宗原装进口的,放相机是在南京找人买的,也是名牌。”老陈补充道:“我们是以旧换旧哎。”陶局长一直是高邮文艺界的朋友,跟我们相处得不错,经不住两个人的好言劝说,终于表态:“唉,换就换吧,就只当我们支持你们工作的,我跟局里其他领导商量一下吧。”
吉普车到了文化宫之后,在省内外看戏并接洽业务,在城乡各单位送票、收款,成天开得不熄火。我们最繁忙的时候,三天接一个剧团。城内到处张贴“吃有食堂,玩有剧场,电话住宿,3576(电话号码)”的宣传广告,单位工作有了新进展,经济效益有了新提高。
1986年,县换届选举大会在文化宫举行。组织上已找副县长朱延庆正式谈过话,不再连任,另有任用。因为大会充分发扬民主,朱老师被许多代表推荐为副县长候选人,大会秘书处按规定将他列入投票选举名单。我在后台,听监票、计票人员统计选票数据,得知朱老师票数很高,肯定众望所归、高票当选时,望望主席台,没有发现他的身影,连忙跑出剧场,找到驾驶员,拉上老陈,跳上吉普车穿街过巷,直接来到了朱老师的家。三言两语后,朱老师匆匆上车,赶向会场。此时,正宣布副县长当选者名单,报到“朱延庆”三个字时,主持人台上台下,四下张望,不见其人。台下的代表们发现朱老师正步入场内,立刻拍起了巴掌,全场上千人的目光聚焦,掌声雷动,这是全县代表对他的尊重和信任,朱老师感动万分。事后他对我说:“我要是不在场,对不起大会代表。真的亏你!”我说:“如果没有吉普车架势,我无能为力,那将是一件憾事。”
也是当年的一天下午,我从电话里得知,曾经的同事金实秋的儿子放学回家途中,因病摔倒,昏迷不醒,在县人民医院抢救。我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,招呼驾驶员把吉普车加满汽油,又带了一桶备用油,直奔人民医院。进了病房,看了看闭着双眼的孩子,向金夫人以及医生了解了情况,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。金夫人说:“文化厅让实秋出差在外,正在联系。”医生说:“我们根据病情已采取了措施,但孩子不见好转。”记得在场的文友一声不吭,不敢插嘴。我提出:“必须请南京专家来邮会诊。”有人说:“派谁去呢?”我说:“我去呀,车子已准备好了,马上出发。”一位女医生说:“明天是星期天呀。”我脱口而出:“不能耽误时间!必须立即走!”她又说:“你不是医生,能把专家请来?”我想了想,说:“请医院开个孩子的病情说明给我,其他事我来想办法。”事后有人说我:“你胆子太大了。”我说:“这并不是我鬼使神差的一时冲动,只要把朋友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,自然懂得应该如何去做。”人命关天,刻不容缓。怀揣医院的说明信,我走出病房向停车场跑去。金夫人追着我痛哭,拜托我不惜一切代价快把专家请来。我挥挥手,不敢回头,因为我自己也被她的悲情感染而落泪了。
吉普车行到仪征附近,路边有个老头子拼命拦车。我叫小吴停车,我下了车询问情况。老头子指着一旁的板车说:“上面裹着被单的是我儿媳妇,赤脚医生说她宫外孕,流血不止。打了几个电话给仪征人民医院,他们不派车来。儿子在外打工,我只好用板车拖她到公路边拦车,拦了半天,没人肯停车。”救人要紧,我说:“你抱着她赶快上车!”老头子抱起儿媳妇上了吉普车,又下车,把板车扔进了路边的田里。小吴问:“往哪儿开?”我说:“这还用问,仪征人民医院!”到了挂号窗口,我掏出《乡土报》社发给我的采访证递给挂号员:“告诉你们领导,患者家里打来过急救电话,你们不派车,宫外孕出血弄不好要出人命的!赶快抢救,我有急事要办,说不定还要来采访这件事!”医院里跑来几位医生,用手推车把患者推走了。我自知重任在身,小吉普像一阵风似的冲向公路,直奔南京。
第二天一大早,找到了省人民医院总值班室。总值班是位年长的女士,一副老干部模样,她看完了病情说明,又耐心听取了我的汇报,还问:“孩子是你什么人?”我说:“朋友的孩子,他父亲刚调来南京,出差在外地。”她被我焦虑、诚实的言语感动,夸奖了我:“对待朋友的孩子能这样做,不简单,我答应你的要求。”随即写了个便条,要我去珠江路找在家休息的专家去高邮,那专家却推辞了。我又心急火燎地坐着吉普车向总值班汇报,她又电话安排家住鼓楼的另一位脑科专家出诊。那人同意了,并立即跟我的车赶往高邮。一路上,我虽然一夜没睡好觉,仍坚持和那位专家热情友好地交谈。专家来到高邮人民医院,他肯定了医生抢救措施及时、得当,但设备条件简陋,必须立即把孩子送往南京。我们的小吉普为抢救突发疾病的孩子争分夺秒,赢得了宝贵的时间,但孩子转院又面临巨大风险。这时,老金已火速从外地赶回了高邮,他站在“二招”门口征求我的意见,我说:“省人民医院已安排病房,专家也同意随车护送,途中又有多家医院,应当毫不犹豫地坚决把孩子尽快送往南京!”他采纳了我的意见。
1987年,我调往南京。离别了相处多年的领导和朋友,也离开了那辆从旧吉普变成的破吉普。
1992年3月,我回高邮闭门修改电视文学剧本《少年李时珍》。有一天去三垛拜访朋友时,一眼发现我曾坐过多年的吉普车静静地停在一堵墙边。仔细打听,是文化宫以6000元的价格将车卖了。我电话向单位领导作了汇报,以原价将车子又买了下来。
到了南京以后,破旧吉普经过修理,整旧如新。随着电视剧《少年李时珍》摄制组成立,小吉普再立新功。在黄山期间,成了导演、摄像专用车,也成了置景、服装的道具车。在拍摄顺利结束的当天。40多位演职员乘小面包、大客车去了南京。我和周导演、美工李乐坐着吉普车选择一条近路回宁。小吉普艰难地爬上了几百米高的山顶,下山时,只见驾驶员甘束手忙脚乱地操纵着方向盘,一会儿摸手刹,一会儿用脚刹,脸色惨白。我问:“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?”从来不发脾气的他大声说:“开车时,请你不要和我讲话!”我吓了一跳,心想,小甘今天怎么啦?吉普车下山的速度特别快,小甘不间断地按喇叭,在山上的伐木工人赶忙躲闪到路边。吉普车一下山,就停靠在路边,小甘满脸汗珠,叫醒后座的周导和小李,大声对我们说:“你们不知道,我魂都吓掉了!下山时,手刹脚刹都失灵了,我已准备撞山啦!”我们如大梦初醒,惊得目瞪口呆。从此,四人成了曾经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
电视剧后期制作是在南京电视台进行的。,临时借用我们的吉普车。这部车刚经过剧组东奔西跑的折腾,又破旧不堪,行驶在繁华的大城市特别显眼。交警挥挥手把车拦下了。司机小甘没有下车,扮演的古月下了车,对前来查车的交警用湖南方言问道:“交警同志,我的车也要检查么?”一代伟人的形象挺立在交警面前,那交警吓了一跳,笑着敬了个礼,“‘主席’,请您上车吧。”
筹备电视剧首演式时,需要一点经费,我们联系了扬子江制药厂,他们答应赞助三万元。同去厂方的有作曲家、歌唱家冯金发,高邮老乡、卫生厅的处长魏鹏和我。办完事返宁,途径六合南行,一个个谈笑风生。老冯说:“唉,人该知足啊,当年在北京检阅部队,坐的就是吉普车!”我也对吉普车的来龙去脉高谈阔论:19世纪30年代,一种顽皮的动物形象,取名为尤金尼吉普,机智勇敢并善于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险境且屡屡化险为夷,正是吉普车的写照。1944年6月,二战中的盟军强行在诺曼底登陆时,指挥官都是乘坐此车,使吉普车名声大噪……
大家正谈得兴高采烈,哪料到,行驶得很正常的吉普车突然左拐撞坏了不锈钢护栏,在公路上旋转三百六十度又撞坏了右边的护栏,然后,稳稳停靠在右侧路边。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,双手紧扶座前的把手,安然无恙,第一个跳下了车。老冯的腿擦破了点皮,老魏的伤情稍重一点,脖子扭了筋。小甘连忙检查车况,除水箱漏水,表面铁皮破裂,主设备皆完好。我到路边农家借了个水桶,在秧田里拎桶水把水箱加满了。小甘发动车子开到不远处的汽车修理厂整修车辆。午饭时,戒了酒的老冯买了一瓶白酒:“大难不死,庆贺一下吧。”开怀畅饮时,老魏说:“万一出大事了,你们是因公献身,我是请假陪你们的,什么名分也没有,岂不悲哉!”我意识到,这辆吉普车确实老化,不能再使用了。
31年光阴一晃过去了。上个月,我和周导、李乐、甘束在南京重逢,谈起往事,不胜感慨。那辆与我生死与共的吉普车早就失去了踪影,但在我脑海里,因吉普车所涉及的一连串的人和事历历在目,始终没有忘却。
原文刊载于《高邮日报》2018年6月19日副刊
本文配图和文字以及音频未注明作者的
敬请作者联系微信君加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