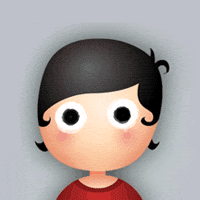美、生活和梦境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。——杨献平
巴丹吉林的军旅生活
A、营盘
按照习惯,我们叫做营区,具像而真实的一种,而在内心的坚韧部位,我们称其为营盘,带有钢铁和神圣的意味。作为营区,它显然很小,落在浩大的戈壁之中,显得渺小和孤单。从空中看,还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。那些树,总共不过10000棵,一棵棵头顶尖尖,满身的绿叶,向着深邃高远的中国西北天空,有如静止的箭矢。两三座二层的楼房上面,彩旗飘飘,在焦黄色的沙漠的衬托下,显得格外生动。就连那些年代久远的红色平房,也在横幅和灯箱之间,洋溢着一种纯朴而结实的力量。最为高大的算是水塔了,在营区之内,甚至更远的沙漠深处,凸出着,成为一种至高,随时都在引领着方向。一条窄窄的马路,从营门开始,直直的,,把两边的营房截然分开。我们上班下班,上机和散步,都经由它的身体。绿树在两旁,一棵棵地整齐排列,像我们在操场上的队列。到了夜晚,灯箱静静亮着,十米一面,标语和图片是一种昭示、提醒和潜移默化。
这是夏天,似乎一直在重复着,在时间的齿轮之内,度量时代和生命。我们总是可以看和感觉到:高空的太阳,热烈的光芒,在我们、树木和沙子的头顶,燃烧着一种激情。而清晨是凉爽的,从沙漠深处吹来的风,经过长途跋涉,似乎洗净了尘土,在我们的脸颊和胸口,传达着一种舒畅的心意。整齐的步伐沓沓响着,一队又一队,开始杂乱,两三步之后,就成为了合声。口号的声音在树枝和绿叶上缠绕。惊醒了那些在灌木中懒睡的鸟雀,一只只地突突飞起,在我们地面前,一跃一跃地消失,鸣声虽然很急促,但似乎没有惊惶。正午时候,营区格外静谧,我们三个五个,经常坐在成排的树荫下面,说着一些事情,更多的关于军事。我们经常比较着,想象、判断和评论着那一些遥远或就在身边的战争。当然,还有个人的家事和爱情,尤其是切肤的爱情,它叫我们总是那么忧伤和激动。远在家乡的那个人,她在纸上的每一个言词,都仿佛是一枚青草,向上或者折断,都会在内心掀起风声。
但这里的冬天太过漫长了,一进9月,风就有些凉了,在我们裸露的手臂之上,制造着轻微的寒冷。这时候,树木显得无精打采,在风中摇晃着,迅速变黄的叶子相互拍打着,哗哗的响声,类似于我们在总结会上的掌声,尽管有点参差不齐。第一枚叶子落下了,在空中旋转,划出优美的弧线,它们也许是快乐的,也许会悲伤,但它们下落的姿态,透着一种坚定和从容。面对这些必然的落叶,我们常常触景生情,说,夏天这么快就过去了,似乎是眨眼之间的事情。
而春天,沙尘暴的世界,那些强大的风:摧毁和塑造的力量,不知道什么时候,它们就开始在巴丹吉林的深处酝酿了。往往,天气的温度有所上升,静止和暖和几天,在某一个黄昏或者早晨,风起来了,首先是浓重的土腥,肆虐我们的鼻腔,就连喉咙里面,也堆满了大批的灰尘,它们蜂拥着,从无形到有形,从稀疏到密集,一颗颗,一粒粒,在风中显得生硬,且棱角分明,划过我们脸庞的时候,可以觉出甚至听见那一种类似刀割的声音。偌大的天空变得浊黄,戈壁滩上的一片浓雾,犹如杀戮的军团,向着我们的营区,汹涌而来。
我们回到房间,整齐的床铺,白色的床单上面落着厚厚一层,用手一摸,白白的,粘在手掌上。关紧窗户,沙子击打着玻璃,屋里突然黯淡,开了日光灯,也还是黄昏的模样。
沙尘暴的消失,大都是两天或者三天以后的事情。天空深蓝,阳光在沙漠的一端,以自己的光芒和步伐,不断向上,计算着我们的一天。每当此时,要不是窗台上的那些灰尘,营院里面的杂草和枯枝,感觉就像一场梦境,突如其来又平静如常。
吃过早饭,我们就端了清水,拿了抹布,到机房去,为设备擦拭积尘,还他们本来的清亮面目。往往,站在高高的光测台上,东风一吹,一股豪气,从心底腾冲而起,一边的戈壁苍茫辽阔,远处的黄沙像是连绵的波涛,在越来越炽烈的阳光下面,闪耀着刺眼的金色。隐约处的汉代烽燧、古关和废城,静立在大漠之中,苍茫、坚韧,张扬着一种绝不妥协的风骨。如果恰逢任务,一抬头,就看见了空中的战鹰,它们在空中不断开辟新的道路,以自己的嘹亮声音和独特姿势,在我们的灵魂之内,刻画着一种生命的澎湃风景。而俯首我们的营区,紧张而安静的营盘,总有一种感情,叫我们倍感亲切和神圣。
B、春天
已经五月了,春天还没有正式展开。远处的戈壁滩上依旧冷清,有些温暖的风持续吹着,不缓不急,就连那些轻浮的灰尘,也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,在空中,在我们的呼吸之内,缓缓飘动。最初几年,我们总是不大习惯,我们想:要是在内地,麦子都扬了花儿,蒿草疯长,就连干燥了一冬的石头,也苔藓满身了。
而这是巴丹吉林,沙漠的边缘,四周的戈壁,流沙汹涌,碎石匍匐……几年之后,我们就习惯了。感觉像沙漠的一粒石子,无动于衷,随遇而安。太多的时候,我们想,春天总会来的,不可避免。而漫长的等待总是在紧张的生活中度过,很多时候,我们浑然忘了,意识也还在冬天的某个部位僵持着。直到向阳处的野草在偶然的一瞥中显出一丝绿色,我们才忽然意识到,春天就要到了,心里不仅一阵激动。
回想起来,当兵第二年,看到那一丝绿色的时候,我一下子怔住了,意识里面有一道闪电,一下子就撕开了我在冬天的心情。满心的盎然和快乐,转身对一边的战友们嚷道,你们看,春天!他们先是愕然,继而一个个离开了自己的座位,快步走向窗户,探着脑袋,往向阳的墙根看。我看见他们的眼睛中闪着晶晶的光芒,就连说话声中,都带着轻微的颤音。
接着就是那些大葱、韭菜等植物了,它们大都缩在菜地里面,在冬天,身子埋在干硬的泥土之下,像一个惯于沉默的智者,再冷再漫长的冬天,它们也始终不吭一声。我想它们比我们更知道,春天一定会来的,只要一丝气息,就可以张扬出一片生命绿色。
这时候,我们就该拉粪和翻松泥土了,先放水湿润了土地,再过上一天两天,地皮干了,就组织了官兵,一个个换了衣衫,扛了铁锨和羊镐,排队,整齐的脚步,整齐的口号惊飞了灌木丛中的灰雀,一只只地忽闪了翅膀,啾啾叫着,飞向另一个地方。这似乎是我们最感到自由和快乐的时候了,走到田地里面,把菜地按班排分了,大家齐声喊叫了一声,既表示坚决服从命令,又表达了心情。
接着是铁锹的响声,在结痂的土地之上,铲着从邻近的牧区古日乃拉回的羊粪,均匀撒了,一个挨着一个,铁锨飞舞,大家说着笑着:玩笑,正事和调侃,每个人的声音里面都类似清澈的水流。我也在其中,每当这个时候,心情总是有些激动,直到现在,我仍旧没有弄清其真正原因。有人唱起了歌谣,很铿锵的那种,歌声平阔的戈壁边缘划动,尽管没有传得很远,没有在山谷中的响亮回声。
而我们是那么愉悦,心情就像风筝,在蓝得叫人无奈的西北天空下面,扶摇直上,有着鹰的姿态。很多的时候,我们在这边唱了,那边他们也要唱,虽然不是一个单位,但菜地紧挨着,我们经常见面,像对自己一样的熟悉,即使有点陌生,但一次次的任务和训练也会引领我们认识。我们是战友,我们崇尚心灵相通。
铁锨和泥土发出沙沙的响声,我们不断深入,它们不断翻出,新鲜的泥土散发着淡淡的香味,对于大多数来自农村的我们,感觉是如此的亲切,正在翻动的泥土仿佛就是家乡的泥土,我们仿佛就站在自己家的田地里面劳作。12年了,在巴丹吉林,在这个军营,伊始的生疏逐渐被热爱燃烧,最初的隔膜已经在日复一日的深入和亲近之中碎冰一样消失。我们常常想,在这个世界上,究竟还有什么比这样一种心灵行为更令人幸福和快乐呢?
不一会儿,汗水就出来了,在额头、脸颊、后背甚至全身,我们摘掉了帽子,脱掉衣衫,只穿一件背心,温热的阳光照耀着我们藏了一冬的皮肤,我感觉到了它的温度,随着细小的毛孔,不断深入,进入身体和灵魂,在血液和骨骼里面,发出令人陶醉的叫喊。这种感觉,我一定细细珍爱,在内心收藏,我要它跟随一生,在我老了的时候,一个人坐在阳光下面,背对阴影,不断地听到它们的声音,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呵!
似乎刚刚一天,一抬头,我们就又看见了绿色,大片的绿色,悬挂在树枝之上。我的第一个感觉是,春天真的来了!虽然有些唐突,但也在我们惯常的意料之内。接着,我就看见营区内外的大批白杨,一棵棵,一片片,纷纷张开了眼睛,伸出了嫩嫩的手掌,向着掠过营房的东风,在我们的仰望之中,茂盛着蓬勃的生命力量。
然而,叶子们的进展似乎有点缓慢,颜色灰白,叶周微卷,一副幼不经事的样子,可爱得叫人心疼。倒是那些榆树,几乎在眨眼之间,原本干枯,且沾满灰土的枝条就被绿叶攻占和掩盖了。接着,是梨花和杏花的香味,它们在巴丹吉林虽是少数,而又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们绽放呢?这一时候,清早出操的路上,枯燥的空气渐渐湿润起来。午睡当中,常常有蜜蜂的声音传来,在那些花朵上面,飞飞停停,衔着一身的甜蜜,陶醉其中。还有一些颜色多样的鸟雀,经常停留在营院中的树枝上面,尖尖的嘴巴里面常常吐出一些喊出叫我们身心轻盈的歌声。
C、我们之间
沙漠太大了,一眼看不到边儿。我们经常到里面去,看见牧人、骆驼和羊群,还有沙鸡、蜥蜴、蛇、小跳鼠、野兔乃至狐狸和黄羊。我们不去追逐,更也不会猎杀,但它们还是十分惊惶,看到我们或者听到异声,这些沙漠的忠实居民,一只只地竖起了耳朵,停止了嚼动,我们稍一走近,眨眼之间,它们就飞出了几百米的路程。我们就对着它们的背影喊,不要跑,我们是邻居,我们友善。有几次,一只肥硕的野兔听到之后,真的停了一下,回头朝我们看了足有两分钟的时间,然后快步消失在一丛浓密的骆驼刺丛中。
倒是那些牧人,蒙古族的朋友,他们就住在沙漠深处的古日乃草原,与营区相距大约200华里。他们时常到营区附近放牧,我们远远地看见了,就喊,他们答应。或者他们先喊,我们在循着声音看见。我们带了干粮和水,就给他们一些,他们有,也主动叫我们一起食用。在一起的时候,我们站在询问一些什么,牧民们的嗓门很大,一个字一个字地浑重清晰,说得我们哈哈大笑。分手的时候,相互伸出手掌,重重相握。
一直叫我们感到奇怪的,这片孤寂干燥的沙漠当中,竟然还有一眼汩汩外冒的泉眼,就在我们营区西边大约5公里的地方。泉水的一边,有一所泥土做的房子,伫立在戈壁之中,再一边是一个用枯树围起的骆驼圈或者羊圈,。每年的夏天,总有人在那里放牧,身披黄色毛发的骆驼走得很远,我们时常可以看见。牧人也经常到营区来,我们给些面粉、水、蔬菜和盐,他们总是感谢,我们总是说不用客气,时间久了,我们都熟悉了,就连刚来的新战士,也很快就叫出了他们的名字。
到了冬天,牧民驱赶着骆驼和羊群,去向了更远的地方,我们也就很少到泉眼的地方去了。大概是他们的羊只熟悉了牧区和营区的路线,经常跑到这边来。最近的一次,是去年的11月,站长带着我们到沙漠搜寻试验残骸,不经意之间,看见6只绵羊,散落在戈壁之间,我们想这应是巴图的羊吧,就开着车子四处看了看,不见羊群,也不见巴图。就捉了,放在车上,把它们拉回营区,交给后勤军需股喂养,一边给古日乃乡政府打了电话。等失主巴图来领的时候,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,巴图看到自己家的羊只,咧开嘴巴,露着黄色的牙齿,嘿嘿地笑了起来。
牧民们养的羊只和骆驼太多了,一个冬天过去了,圈里积了厚厚的一层土粪。就要翻松菜地了,巴图或者其他的牧民打电话或者骑摩托专门跑来,对我们说,去我那里拉粪吧,一分钱都不要,我们说那怎么行呢?巴图噘嘴说,那怎么不行哩。我们去了,带着几袋面粉,大棚蔬菜和几身新军装。我们车队浩浩荡荡,在沙漠之中左冲右突,车后面腾起一团一团的白烟,不一会儿,绿色的军车就变成灰白色的了。
大约3个小时,100多里路程,就到了巴图的家。第一次去的时候,我没有想到,巴图竟然一家人住在一个地方,四周不见人烟,空廓得让人丧失时间观念和方向感。远远的,就看见巴图、巴图的爱人和两个七八岁的小孩,站在房子的一角,向我们挥动着手掌。下了车,巴图一一和我们握手,重复说着“塌塞白浓”(你好),他的妻子站在原先的位置,头上包着一面红色的头巾,黑红的脸上漾着喜悦的笑容。他的两个小孩早就蹦哒起来了,跟在巴图的后面,用汉语喊叔叔好。
卸了带来的面粉和蔬菜,稍作休息,我们就开始装羊粪了,巴图趁机宰杀了两只大羊,熟练地剥了,用大刀砍做数块,放在已经滚开的大锅里。我们休息的时候,巴图的妻子拿出了自己酿制的酸奶和奶酪。装完了车,我们说要走,巴图一家拦住说,怎么也得吃了羊肉再走,我们说不行,一定要走,巴图急了,站在车头前面。我们只好坐下来,巴图拿出烈酒,和我们盘腿坐在炕上和羊毛地毯上,吃起了羊肉,除了司机之外,都端起了酒杯。一会儿,就唱起了歌谣,歌声在空空的戈壁之上,虽然传不了多远,而在我们心中,它音律铿锵,回声隆重。临走的时候,在饭碗下面,我们没人压了20元钱。等巴图发现的时候,我们的车队已经驰出了好远。
在我们的记忆中,从我们认识时候开始,巴图一年要来营区十几趟,虽然夏天经常在戈壁中碰见。巴图说,他喜欢到这儿来,隔上一个月不来,心里就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。我们也欢迎,他来了,就和我们一起吃饭、休息,聊一些各自的事情和想法。后来,其他的牧民也跟着巴图来,时常一长,牧民们不管认识不认识,也常到营区来。一晃十二年过去了,巴图渐渐老了,我的那些战友大都离开了,我也由士兵成为干部,时间这东西,快捷得叫人猝不及防而又无所适从。今年初春的一天,一个打扮入时的男人来到营门外,卫兵不认识,我们也不认识,样子看起来也不像牧民,心里就有点怀疑。我们就问,他说他是巴图的儿子,叫铁木尔,现在甘肃民族学院历史系读书。我们笑了,问巴图大叔还好吧,他说还好,只是关节炎病疼得厉害,不能走太远的路程。
D、叫人心疼的雪
星期天早上总是起得很晚,这几乎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。雪下来的时候,我们还在早睡。而雪——巴丹吉林的雪,简直就像一场温柔的爱情,不知不觉间席卷了我们的梦境。我根本没有想到,常年干旱少雨的巴丹吉林沙漠,竟然在这一个初冬的早晨,把一些来自天堂的精灵挥洒下来,轻盈得犹如我时常在梦中看到的唱着歌谣的白色蜜蜂,不声不响地,给干燥得满身伤痕的巴丹吉林沙漠带来了那么多令人心碎的美。
我起身打开窗户的时候,看到了她们。我一阵惊愕,怔怔站在窗前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,在内心企盼已久的雪会在这一个极为平常的早晨,从遥远的高空飞跃而下,来和我们这些和沙漠一样干燥的生命相见。
——雪花仍在继续,一颗接着一颗,一颗挨着一颗,前前后后,纷纷扬扬,满天飞舞,曾经堆满石砾和黄沙的地面已被她们掩埋了,雪密密艾艾,将我们的视线铺排成一片白色的海洋。我急忙叫醒妻子,她欢呼着,从床上蹦起来,像个小孩子一样,一下子就扑在窗玻璃上,冲着外面的雪大声呼喊。她的表情揭示了她内心的兴奋,她倚在我的肩头,一个劲儿地跳着叫着。她的兴奋深深感染了我,我知道,对雪,所有在这里生存的人,都怀有一种极其美妙的情愫。我敢说,在我们——在同在这一片沙漠生存的每一个人心目中,怀念雪,喜欢雪,决不仅仅只是一种外在的享受,而是一种深入心灵的灵魂渴望和精神沐浴。
雪从来就是一种象征,一种超越了时空、地域和种族的神圣的美。我在巴丹吉林沙漠生活了10年时光,这一场雪是个人记忆中的第二次心灵盛宴。我还记得3年前的那一场雪,当我看见她的时候,竟然一个人跑到营区外的戈壁滩上,静静地站在空旷的天幕下,任雪花飘落,在我的身体之上安身成家。我在那里一个人站了近一个小时,在那种静谧的氛围中,我仿佛听见了自己血液逐渐减缓地流动声,听见了自己骨骼轻微的脆响。很快地,自己竟然和白茫茫的大地融为一色,在那时的感觉中,感觉自己纯洁得就好像一粒雪花似的,整个身体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和轻松。
而今,大批的雪又一次莅临巴丹吉林沙漠,对我来讲,就像一位阔别千年的朋友,或是一位梦寐以求的美丽姑娘。她的来到,使我本来很忧郁的心情突然开朗起来,在打开窗户的那一刹那,我的脑海里到处都是洋洋洒洒的雪花,除此之外,什么都不见了踪影。三年前的那种纯洁感觉再一次袭击了我的灵魂。可是,一个人不可能长时间地被一种事物吸引而陶醉。生活是真实的,在我的思想中,总认为真实的生活就是雪花掩埋下的石砾和黄沙,一颗颗、一粒粒,坚硬而又永不确定。我也知道,雪花的覆盖是暂时的,真正美的东西总是容易消逝。这是人类的共同的悲哀,是上帝或者冥冥之神对我们的一种善意嘲弄。
我也看见一些人,在用扫把使劲扫着堆满路面的雪花,他们吃力而虔诚。我知道,他们是一种好意,是怕那些老人和小孩不小心滑倒。可在我看来,雪花也是一种自然行为,她们爱落在哪里就落在哪里,什么东西都不可干涉。其实,扫雪本身也是对自然的一种不尊重。
妻子已经穿好了衣服,拉着我的手,要到雪地上去。我们锁好房门,像飞的一样,从楼梯上跳下。,平得像块地毯。我们站在那里,只是看着,我们不忍践踏那片纯洁的雪地,这难逢的美好世界,哪怕人的力量和科技再伟大先进,也不可能一下子就作出这样一片雪地。我们的双脚一旦踩上去,这一片雪地就会变得面目全非,就像美丽姑娘脸上的疤痕一样。这对于唯美的人来说,是很残酷的。
我和妻子走出院子,脚下的雪发出骨头断裂的声音,脆脆的,我对妻子说:这是雪在叫喊,是对咱们的一种抗议和谴责。妻子笑笑说:是不是鞋底太脏了?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,什么样的回答都是多余的,雪已经被我们踩在脚下,即使是过错,我们也没有挽救的机会了。当事实出现,所有的辩解都等于谎言。
出来踏雪的人们三三两两,他们拿着相机和摄像机,在雪地上照着,他们想把这一场雪留存在自己的生命轮迹中,更想雪花把自己衬托得更为伟岸或是靓丽一些。这是我们的共同心情,雪是不会在意的。但有雪的衬托人就会更干净和美丽吗?把雪留在生命轮迹中就等于自己拥有了雪吗?人有时显得很可笑,尽管可笑,每个人还总会这样想。
我们走到戈壁边沿,厚厚的雪地昭示着两行清晰的脚印。戈壁的硬风迎面吹来,刀子的感觉让我们的脸庞疼痛。妻子说,咱们堆一个雪人吧。我们的双手伸向雪花,一把把地捧起来,使劲儿把她们捏在一块儿,雪花的冷深入到了我们的骨髓,我们感到一种淋漓的疼痛。很快地,一个小小的雪人堆起来了,鼻子、眼睛、头发和肥肥的身躯,像个幼稚可爱的孩子,冲着我们甜甜地笑着。可雪花总要消逝的,这是我们共同的宿命。当我们渐渐走远,那个幼稚可爱的雪人,就有和远处的雪地融在了一起,就像我们渐渐融进来来往往的人群一样,美、生活和梦境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。
E、亮色
越过戈壁,在沙漠深处,我们可以看得更远,只是那些松软的黄沙,平静的起伏,却有着埋葬的危险和吞噬的杀机。刚来的时候,我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人居住、工作和生活
从我们所在营区出发,出了营门,就是戈壁滩了,一丛一丛的骆驼刺漫无目的地生长着,根茎上结满尘土,裤脚或者手掌稍微一触,就抖起一团浓浓的灰尘。夏天时候,傍晚,我们总是要去那里散步,几个一伙,踏着硬硬的沙石,抬头是西冲的落日,以七色的晚霞作为陪伴;低头是黑色的碎石,动物的足迹和地鼠的幽深洞穴。
而要到那个小点,需要乘车,30公里的路程足够一台解放和北京吉普跑一个多小时。车轮一旦接触到戈壁,灰尘就起来了,虽然有一条车子压了不知多少遍的路,但很多的地方浮土厚重,一些经验不足的司机经常在它们那里抛锚。其实,什么事情都一样,熟能生巧,跑得多了,司机就了如指掌了,跑起来得心应手。车子大幅度地颠簸着,我们紧握着扶手,全身崩了劲儿,不使自己身体碰在一边的钢铁。即使这样,脑袋也难免碰到车顶,一下一下的,令人猝不及防。
即使密封程度再好的车子,也阻挡不了无孔不入的细尘,这些善于钻营的投机者,只要稍微有点缝隙,绝对不会放过。但也不可排除车子本身的问题,很多东西根本上是内部的原因。在这样的路上,我们几乎没有闲暇左右看看,目光盯紧前方,不断迎面而来的戈壁,在我们的凝望之中,始终是一种无动于衷的姿态,仿佛临危不惧的勇士,面对迅速奔来的钢铁,没有一丝的惊惶和不安。
其实,一条路就是一种过程,既是肉体的也是生命的。接近的时候,那个小点就出现了,在昏黄色的戈壁当中,数株绿树,掩映着数座雷达和光测塔罩,在这二者之间,灰旧的营房显得尤其低矮。营门很窄,只可以容一辆卡车勉强通过。也没有战士站岗,想来也不需要,这沙漠的纵深地带,除了领导和机关的人,一般不会有什么人来。两边的红砖墙上写着一些口号和标语,最显眼的当数“身在沙漠,。看着那些红艳艳的大字体,我心里就有点激动,在一色枯燥的沙漠,多一种颜色就多一份生机,至少也是一种填补。营区里面,是两排左右正对的房子,正西是饭堂。两边是一色的杨树,绿油油的叶子风中不断地忽闪着,拍打着。院子很宽,篮球架和排球网各占一边。许多的战士只穿了背心和短裤,在场上叫喊着,奔跑着,左冲右挡,闪跃腾挪,小小的篮球和排球在空中飞来飞去,煞是热闹。
这时候,正是2003年的五一放假期间,不仅任务繁重,而且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自然灾害。我们没有惊扰他们,倒是一个在一边看球的战士飞身跑回营房,不一会儿,教导员郭广彬出来了,快步走到副站长冯治国面前,立正,敬礼。我就在一边站着,看见郭广彬的脸上,丰盈着一种喜悦和激动的笑容。张口对我们说,一个月没有见到外面的人了,语气里面有些遗憾和感伤。说着就把我们往大队部领。走到门口的时候,一个小男孩蹦跳着从里面跑了出来,看到我们,飞快地冲我们喊了伯伯和叔叔。不用告诉,我们也知道这是郭广彬的儿子。冯副站长说,一家人都到这儿来了。郭教说是的。
其实,我在政治处工作的时候,写过关于这个小点的典型事迹材料。其中专门提到了郭广彬的夫人马冬艳,郭广彬到这个单位任教导员两年多了,每当小孩放假,夫人马冬艳就带着来到小点,与郭广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。
我们深知,对于常年生活和工作在沙漠深处的官兵来说,对于异性,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。记得我在另一个小点的时候,还偷偷地在戈壁滩上写过一些至今想起脸红的话。对此,我不以为有什么错误,至少是一种生命的自然和本真欲求。马冬艳的到来,无疑给这个小点带来了一抹亮色。时间一长,相互熟悉了,官兵把轻易不说出的秘密都说给了马冬艳,主题内容无外乎请嫂子介绍对象之类的个人私事。马冬艳听了,也记在心上,回到师部所在的营区之后,穿针引线,两年时间,促成了几对,其中两对已经结婚,还在三对正在进行中。
说完了这些闲话,我们这次来的任务也快完成了。临走的时候,郭广彬和马冬艳一直送到营门口,走了一段路程,我再回首,他们还站在路边,朝我们看。看着他们逐渐变小的身影,突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情绪,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,在我的内心,缭绕着,游动着,遍生感慨。
F、南沙山
一抬头,就看见了,在营区内,我从宿舍出来,走出一段柳树的排列,转身,向东,抬眼,它就在那里了。更多的时候,它是静止的,在沙漠上面,微微隆起,与我们的目光保持平视,视觉绵软,内心亲切。
每天早上和傍晚,是它最美的时候, 尤其是夏天,太阳刚刚升起,光芒打在我们身上,温和、均匀而散漫,耀着领章和帽徽,连同眼睛,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发光物件里面,都晃动着一颗太阳。目击的南沙山,也满身金黄,就连背阴的凹陷处,丝绸一样披散。
风在沙漠的腹腔还没睡醒,鼻息幽微。这应当是风对我们的一种仁慈,不忍再打搅我们被它撕扯了一宿的心情,也使我们能够又一个忘却和改善心情的机遇,以坚定我们日复一日在它一边生活和工作的信心。这里面似乎含有一种欺骗和诱导的意味,但我们已经习惯了,也愿意接受。而南沙山,作为一种流沙的流浪和积攒,它的皮肤不断更换,更多的沙子从我们看不到的地方,或者百里之遥,或者就在身边,来历不明,像我们一样,阅历简单,而方向多变。
我们知道,它是流动着的,沙漠和风运动的结果,只是觉察不到,多少年了,它的姿势不曾改变,这是在我们的感觉和眼光,事实上,它不断运动,变小、扩大,每时每刻,就像我们的年龄、职务和心情。我经常感慨,内里的流动,往往与表面联系不大。就像我和我们,很多时候,内心惊涛骇浪,樯倾楫摧,但脸色仍旧一潭止水。
作为一个人,谁的心里会没有风呢?
风在人的内心,蟒蛇一样的硕长、柔韧,我们并不清楚它们的首尾具体何向。
作为一种仅在咫尺的风景,一种事实,实际上也是一种安抚。每年的“五四”,我们都要去一趟,算是春游。在沙漠,在这个军营,除了南沙山,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的呢?这似乎有点狭隘和残忍。但好在有一处令我们产生欲望的风景,这多少是一种对长期枯燥心灵的勾引乃至滋润。需要说明的是,在这个名叫巴丹吉林的沙漠边缘,我们常常遗憾,近处的戈壁和远处的沙漠过于平坦、粗砺、毫无起伏和一览无余了,即使有心仪的女子,可连一个约会,甚至偷情的地方都不予施舍。
出了营区大门,彩旗飘起来了,在我们的肩头和头顶,在戈壁之上,蓦然一片嘹亮,歌声响起来了,在空廓之中,溅不起一丝声响,尽管声音在我们的嘴巴和胸腔,有着雷和风的动静。脚下的粗沙和碎石,身边的骆驼刺和梭梭草不断摇晃着蓬开的身子,细碎的尘土犹如戈壁喷吐的烟圈。平时不多见的沙鸡和野兔在前方或者一侧,突突飞起,仓皇奔跑。我们打搅了它们的安静,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。对此,我们大概没有歉疚,我们由来已久的自大、麻木习性,根深蒂固。
戈壁褪去,就是一色的黄沙了,高高低低,依次隆起,一直到了需要仰望的高度。背后是蓝得要命的天空。一顶一顶的沙丘,硬硬的,挺挺的,光洁的,干净的,时常忍不住要抚摸。我时常为这一念想感到羞惭,但又一想,太多的无力的美,似乎用来摧残。这时候,阳光炽烈起来,提升着黄沙的温度,沙子从鞋口涌入,双脚发烫,行走在火焰之上的感觉,我们索性脱了鞋子,光光的脚丫,在平静的沙坡之上留下伤疤,一道一道,扭曲得叫人心疼。但我们也似乎没有觉察,向上的顶点的欲望占据了心情,我们喊着,跑着,一个个撅着屁股,扭着粗细不一的腰肢,气势有点像攻占高地,样子却类似笨猴爬杆。我在后面,气喘嘘嘘,全身的汗水拧着肢体。
至山顶,截然一面刀刃,曲曲弯弯,好一道优美的线条。一边是幅度平缓的沙山,一边则是刀切一样的深渊,足有300米之深。深渊的一边,就是干硬的戈壁了,一直向北,伸展着辽远。而向南的一面,沙坡起伏,沙丘连绵,一座一座,诗歌一样的沉着、幽静、闲适和优雅,有着无意炫耀的意味和随其自然的开放姿态。而我们知道,这些都是暂时的,包括我们留在其上的那些脚印和躺倒的痕迹,也许就在今晚,就会消失得跟没有一样。我们都想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留下一些自己的东西,而什么东西才是真正能够留住的呢?沙漠、戈壁乃至它们造就的这座沙山,有一天也会消失,所不同的是,它们的消失我们无法看见,而我们的走远乃至消失却在它们的目睹之下。
旗帜更为猎猎了,风在鼓荡着它们的单薄的躯体,我们把它们插在沙领上,坐在下面,照相、喝水、吃东西,大声说笑,这时候,我敢肯定,每个人都是快乐的,我们的快乐基本源于这座沙山,而沙山快乐吗?我们不得而知。返回的时候,我们排成队列,从一侧刀切一般的深渊,贴着浮沙滑了下去,松软的黄沙载着我们的身体,连同手中的旗帜,从至高处到最低处,仅仅几分钟的时间,而其间的感觉,有一些快感,有一些惊惧,回首仰望的时候,还有一些莫名的感伤:向上和向下,速度、心情、方向和结果泾渭分明,内心惊诧,但无法出声。
抱紧你的我,比国王富有。失去你的我,比乞丐落魄。——《国王与乞丐》